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微软在史蒂夫·鲍尔默的领导下奄奄一息,后来靠萨蒂亚·纳德拉的神奇领导力才得以起死回生。这几乎是我在所有相关网络讨论中的主流观点,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广为流传。虽然我这篇文章对纳德拉的领导能力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但这种说法低估了鲍尔默在微软成功中所扮演的角色。鲍尔默时期,微软的财务状况、营收和利润不仅亮眼,而且还进行了许多深远的长期投资,为微软在他卸任后的几十年里持续成功奠定了基础。当时,这些投资饱受诟病,说明它们并非显而易见,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当时饱受批评,微软仍然做出了非常明智的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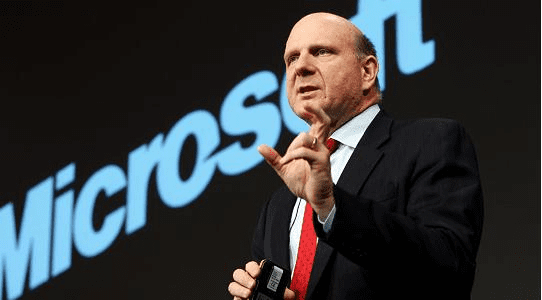
除了主导对后来被人们归功于纳德拉的领域的大量投资之外,鲍尔默还为纳德拉的成功扫清了政治障碍,确保任何继任者都能顺利接任。就像加里·伯恩哈特的演讲一样,由于他把问题和解决方案说得太直白,以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学到了什么重要的知识,所以那次演讲遭到了批评。鲍尔默为微软未来的成功奠定了如此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因为他的继任者如此成功而批评他是个无能之辈。
对鲍尔默的批评
对于那些在世纪之交,也就是90年代之前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微软曾经被认为是业内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公司。但没过多久,人们对微软的看法就发生了改变——到了2007年,许多人认为微软会成为下一个IBM,保罗·格雷厄姆也写了《微软已死》一书,他在书中指出,认为微软高效的时代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
几天前,我突然意识到微软已经死了。当时我和一个年轻的创业者聊起谷歌和雅虎的区别。我说雅虎从一开始就被对微软的恐惧所扭曲,所以才把自己定位成一家“媒体公司”而不是一家科技公司。然后我看着他的表情,意识到他根本没听懂。这就像我跟他说八十年代中期女孩们有多喜欢巴里·曼尼洛一样。巴里是谁?
微软?他什么也没说,但我看得出来他不太相信会有人害怕他们。
这类评论通常伴随着微软营收注定下滑的论调,例如格雷厄姆的以下评论:
演员和音乐家偶尔会东山再起,但科技公司几乎不会。科技公司就像抛射物,转瞬即逝。正因如此,在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任何问题之前,你就可以断言它们已经走向衰亡。相关性可能比营收提前五年甚至十年显现。
谷歌
格雷厄姆将谷歌和互联网列为微软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讨论。虽然格雷厄姆在《微软已死》一书中没有点名鲍尔默,也没有提及鲍尔默的影响,但几十年来,鲍尔默一直是科技圈人士最爱攻击的目标。鲍尔默最初在公司负责业务,后来成为销售和支持执行副总裁;科技圈人士总是喜欢贬低非技术人员¹。过去和现在,人们普遍批评鲍尔默不懂技术,领导能力差,因为他只懂销售和利润,只会照搬别人的做法。举个例子,如果你看看2012年鲍尔默赶走西诺夫斯基时,科技论坛(minimsft、HN、slashdot等)上的评论,就会发现鲍尔默的领导能力几乎遭到了一致抨击。以下是一位自称匿名微软内部人士的评论:
解雇鲍尔默。裁掉40%的员工,先从业绩不佳的在线服务部门开始(这些部门永远不会好转)。把节省下来的数十亿美元重新投资到普吉特海湾地区的初创企业,这些企业能够为微软及其收购目标带来增值……重做Windows系统——包括桌面和平板电脑。认真对待企业云(比如Salesforce……)。

鲍尔默为自己辩护的方式是指出,市场似乎低估了微软的价值。他指出,当时微软的市值相对于其基本面和财务状况而言,远低于亚马逊、谷歌、苹果、甲骨文、IBM 和 Salesforce。鲍尔默的这一评估似乎相当准确,因为自那以后,微软的表现已经超越了所有这些公司。
纳德拉担任CEO后,微软市值飙升,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鲍尔默扼杀了微软,公司在纳德拉扭转乾坤之前一直举步维艰。你可以选择其他讨论,但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看看“微软已死”最近一次登上HN热搜榜首,只需快速搜索一下,鲍尔默的名字就出现了24次。鲍尔默也有一些支持者,但“鲍尔默拖了微软后腿”这种老生常谈的说法依然存在,甚至有一位支持者也引用了部分老生常谈:鲍尔默是个缺乏想象力的庸才,但他至少为微软打下了良好的财务基础。如果你看看那些高赞评论,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在抨击鲍尔默。
如果你浏览一些信息不太灵通的论坛,比如推特或Reddit,你会发现同样的攻击,但鲍尔默的支持者却少得多。在推特上,当我搜索“鲍尔默”时,前四个结果都毫不含糊地嘲讽他。第五个结果褒贬不一,但从评论来看,似乎普遍被认为是在贬低鲍尔默。我向下滚动浏览,除了一个视频之外,其余的视频都在嘲讽鲍尔默(那个视频是鲍尔默接受采访时提到,他在2009年曾出价“200亿美元以上,大概是这个数”收购扎克伯格的Facebook,这在当时将是史上第二大科技收购案,仅次于卡莉·菲奥莉娜在2001年以250亿美元收购康柏)。在Reddit上搜索(使用隐身窗口并清除浏览记录)的情况也类似(不包括关于他作为NBA老板的报道,他在NBA球迷中很受尊敬)。头条新闻嘲讽他,下一条新闻指出他比比尔·盖茨更有钱,而对他的CEO表现的最高评价是“讽刺的是,他是微软最糟糕的CEO”,然后是老生常谈,认为公司业绩好的唯一原因是纳德拉力挽狂澜,鲍尔默错过了科技行业所有重要的变革等等。
总而言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一直嘲笑鲍尔默是个不懂技术的笨蛋,充其量只是个只会算账的会计,他只知道如何维持公司运转,却不懂得如何促进创新,导致微软在每个重要市场都落后了。
鲍尔默的胜利
这种普遍观点与鲍尔默领导下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相符。自格雷厄姆宣布微软“死亡”以来,鲍尔默在财务方面取得的实质性积极成果包括:
2009年:Bing上线。这被认为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但这里的标准相当高。快速的网络搜索显示,Bing据称在2015年盈利10亿美元,并在2024财年盈利64亿美元,营收为126亿美元(考虑到微软2022年的市盈率,粗略估计Bing在2022年的估值约为2400亿美元)。
2010年:微软创建Azure
我个人并不喜欢云产品,但就大规模云基础设施的运行而言,亚马逊、谷歌和微软这三家公司遥遥领先于其他所有公司。从商业角度来看,对微软最严厉的评价也不过是它在业务上稳居第二,并且是成为第一的最大威胁。
在鲍尔默领导下建立并发展壮大的企业销售部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Azure和Office成功的关键所在。
2010年:Office 365发布
微软已将其企业/商业软件套件从盒装软件转型为提供在线选项的订阅式软件。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日期;Office 365 正式发布那一年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和 Azure 一样,我个人并不喜欢这些产品,但如果微软拆分成多个主要业务部门,企业软件套件业务部门或许能在市值上与 Azure 匹敌。
当然,微软也犯过不少重大错误。2010年至2015年间,HoloLens是微软最大的赌注之一,仅次于Azure和Bing,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AR或VR领域的重大投资能够获得理想的回报。微软未能占领移动市场。尽管Windows Phone普遍受到试用者的好评,但不同的人对微软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要么是入局太晚,要么是微软不愿意长期补贴Windows Phone。虽然.NET至今仍在使用,但就市场份额而言,.NET和Silverlight并未兑现早期的承诺,而且由于内部政治斗争,一些关键部分遭到削弱甚至扼杀。Bing的声誉不佳,而且至少就微软当时的处境而言,它可能需要对谷歌提起反垄断诉讼才能成功,但即便如此,Bing仍然创造了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业务部门。尽管存在诸多失败,但微软最大的赌注——Azure——其价值可能高达万亿美元。
微软的企业销售部门在鲍尔默担任CEO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他曾担任销售与支持执行副总裁,实际上最初加入微软时是第一位业务经理),并在他担任CEO期间继续发展壮大。微软的销售策略非常有效,以至于在我任职微软期间,谷歌会向部分Office 365用户免费提供其企业套件(例如Google Docs)。微软的销售人员注意到,即使面对谷歌免费赠送产品的竞争,他们通常仍然能够成功售出微软的付费产品。对于企业客户而言,微软的产品组合及其企业销售团队的强大实力使得谷歌即使免费赠送产品也无济于事。
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并且你在一家“科技”公司工作,那么公司极有可能选择谷歌企业套件而不是微软企业套件,而微软销售人员的企业销售说辞在你听来可能很荒谬。
我认识的一位创业者,曾遇到一位微软Azure的销售人员上门推销Azure,开场白就是:“你们现在用的是AWS,消费级云。你们需要Azure,企业级云。” 对大多数科技公司的人来说,“企业级”几乎等同于价格过高、不可靠、垃圾产品。就像人们很容易嘲笑鲍尔默,因为他出身于销售和业务部门一样,听到企业级销售话术也很容易让人觉得可笑,但总的来说,微软的企业销售部门做得不错。我曾在Azure工作过,研究过它的运作方式,刚从谷歌过来的我,感觉简直天壤之别。那是2015年,纳德拉执掌微软时期,但真正让微软得以大规模扩张的企业文化和流程,却是鲍尔默一手打造的。我记得有好几个月,微软招聘和培训的销售人员数量都超过了谷歌的总员工人数,而且销售流程的每个环节都相当高效。
鲍尔默领导下的微软的失误
当人们列举Bing、Zune、Windows Phone和HoloLens等一长串失败案例,以此证明鲍尔默是个笨蛋,拖累了微软的发展时,这恰恰暴露出他们对科技行业的无知。这就像列举风投公司投资的失败案例,以此证明风投公司不懂行一样。但在风险投资这种以成功为导向的行业,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如果你想指责风投公司不好,你需要指出其总回报率低,或者缺乏重大成功案例,因为这些都意味着总回报率低。同样,像微软这样的大公司拥有大量的投资项目,一个成功的投资足以弥补大量失败的损失。鲍尔默的批评者无法指出微软总回报率低,因为在他执掌期间,微软的总回报率非常高。根据计算时间的长短,从140亿美元或220亿美元增长到830亿美元,具体数字取决于你选择从鲍尔默1998年7月就任总裁还是2000年1月就任首席执行官算起。鲍尔默离任时,公司盈利状况也相当不错,前四个季度盈利270亿美元,超过了他接手时公司的营收。按市值计算,仅Azure一项就足以跻身全球十大上市公司之列,而剔除Azure的企业软件套件可能也只能勉强挤进前十。
因此,批评者也无法指出鲍尔默执掌微软期间缺乏成功案例,例如Azure的创建、微软企业软件从本地桌面应用套件向Office 365等产品的转型、打造全球最高效的企业销售团队、以及创建微软视频游戏帝国(鲍尔默担任CEO期间,微软收购了Bungie,并将《光环》打造成2001年Xbox主机首发时的旗舰游戏)等等。即使是普遍被认为失败的Bing,根据其最新公布的营收和市盈率,也能跻身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第12位,介于腾讯和ASML之间。人们在攻击鲍尔默时,总是拿Bing说事,认为它是鲍尔默执掌期间的失败案例,这恰恰说明了鲍尔默的成功程度。大多数公司都希望自己的成功案例能像Bing那样成功,更不用说失败案例了。当然,如果鲍尔默的远见卓识使他的所有投资都成功,微软的市值达到10万亿美元而不是如今区区3万亿美元,那当然更好。但批评鲍尔默说他有过失败,也有过一些价值1万亿美元的成功案例,这实际上是在说他远非史上最伟大的CEO。没错,但这算不上什么批评。
与纳德拉不同,鲍尔默接手的并非一家唾手可得的成功企业。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鲍尔默上任不久,微软就被视为一家乏味、无关紧要的公司,甚至被认为是下一个IBM,这主要是由于比尔·盖茨担任CEO期间的一些决策造成的。作为微软早期的高级员工,鲍尔默也对当时微软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因此微软的问题至少部分要归咎于他(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微软在90年代取得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尽管如此,他还是妥善处理了微软最棘手的问题,并为继任者铺平了道路。
此前我们提到,保罗·格雷厄姆将谷歌和互联网的兴起列为微软在2007年之前走向衰落的两大原因。正如我们在之前关于科技领域反垄断诉讼的探讨中所提到的,这两者有着共同的根源: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如果我们查阅微软反垄断案的文件,就会发现微软显然预见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控制互联网的计划。作为这些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利用其在桌面领域的垄断地位扼杀了网景公司。从技术层面讲,他们因此输掉了反垄断诉讼,但从实际结果来看,微软基本上从法院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针对微软采取的补救措施普遍被认为毫无用处(最初的判决是拆分微软,但他们在上诉中推翻了这一判决),而且案件拖延了太久,以至于在案件最终判决时,网景公司已注定走向衰落,而那些并非专门针对网景公司的补救措施也毫无意义。
微软曾讨论过一个旨在主宰互联网的计划,但最终并未实施,那就是扼杀谷歌。如果我们像保罗·格雷厄姆那样,以微软的“危险性”——即它如何有效地打压竞争对手——来评判它,就像格雷厄姆当年断言微软已死那样,那么微软的危险性无疑降低了。但微软内部普遍认为,他们是迫于形势才采取了这一行动。扼杀谷歌计划的一部分是将输入google.com的用户重定向到MSN搜索。当时Chrome浏览器尚未问世,移动互联网也还远未发展到任何有意义的阶段。Windows桌面浏览器的市场份额高达97%,IE浏览器的市场份额则在80%到95%之间波动(具体数值取决于年份),其余大部分市场份额则被迅速衰落的网景浏览器占据。如果微软真的采取了这一行动,谷歌将在Chrome和Android系统正式上线之前就被扼杀。除非采取极端的反垄断措施,例如拆分微软,否则微软至今仍将掌控互联网。至于甜点,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理由将矛头指向亚马逊。
经过内部辩论,微软最终没有扼杀谷歌,并非出于对反垄断诉讼的恐惧,而是出于对随之而来的反垄断诉讼所带来的负面公关影响的担忧。如果微软真的将流量从谷歌转移出去,其对谷歌的影响将会比当年针对网景的行动更加迅速和严重。而且,在司法部赢得针对微软的另一项诉讼之前,谷歌很可能就会重蹈网景的覆辙。如果你当时不在场,或许很难想象,但司法部诉微软一案当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其盛况至今未见(部分原因是各公司吸取了教训——据说谷歌通过游说活动平息了2011-201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其提起的诉讼,并且巧妙地应对了最近的案件,使其不再像当年那样占据新闻头条)。自微软反垄断风波以来,最接近的事件是媒体对Crowdstrike宕机事件的反应,但与司法部诉微软一案相比,那只是昙花一现。
如果要批评鲍尔默,或许可以这样说:微软没有像其后起之秀那样,在反垄断案发生之前就吸取教训。一位足够有远见的管理者本可以像谷歌在2011-2012年那样,大力游说以阻止反垄断案的发生;或者像谷歌在当前案件中所做的那样,巧妙地将反垄断案淡化成普通的新闻事件。另一种可能的批评是,微软没有正确解读政治风向,没有意识到在针对微软的那场大案之后至少二十年内,美国不会对科技行业进行严格的反垄断审查。原则上,如果鲍尔默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能够预见到美国即将进入一个科技行业反垄断审查力度减弱的二十年时期,他本可以推翻当初没有扼杀谷歌的决定。
就批评而言,我认为前一条批评是正确的,但除非你认为CEO永远不会犯错,否则这并不能构成对鲍尔默的控诉。因此,作为鲍尔默是一位糟糕CEO的证据,这条批评非常站不住脚。而且,后一条批评是否正确也尚不明确。谷歌能够逃脱惩罚,比如在安卓系统中硬编码搜索引擎,阻止用户更改搜索引擎设置,或者让恶意软件安装程序诱骗用户将Chrome设置为默认浏览器。尽管如此,谷歌仍被视为“好人”,并未因此受到太多审查。而微软却没有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如此宽容对待。直到2011年,谷歌才引发了一场严肃的反垄断调查。因此,2001年至2010年间缺乏严肃的反垄断行动,很可能是因为微软谨慎地规避了反垄断审查,而谷歌当时规模太小,不足以引起关注。如果在谷歌还有机会被扼杀的时候采取行动,很可能会招致严肃的反垄断审查,并引发另一场公关风暴。鲍尔默接手的这家公司,其处境比竞争对手更为艰难,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微软被认为束手无策,而且可能确实如此。如果谷歌采取同样的行动,微软可能会因此受到严厉批评,而谷歌采取同样的行动则会被誉为高明之举。
我在微软的时候,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11年谷歌正式公开指责微软存在不道德行为,媒体对此大肆报道,将其视为微软又一个不良行为的例证。我跟一些微软员工聊过,他们对此感到不满,因为据他们说,微软也是在注意到谷歌的做法后才想到要这么做的。但是,声誉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盖茨担任CEO期间采取的行动极大地削弱了微软的应对能力。
鲍尔默接手微软后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其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作为一位几乎从公司创立之初就效力于微软的资深员工,他对此负有一定责任。但鲍尔默成功地清除了董事会中最糟糕的害群之马,使得纳德拉不必接手如此棘手的局面。如果我们探究鲍尔默领导下的微软为何未能主导互联网领域,除了担心扼杀谷歌会引发公关危机之外,内部政治斗争也扼杀了微软大多数最有前途的网络产品,并削弱了其余大部分网络产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例如,早在1997年,也就是谷歌成立前一年、谷歌收购Writely前九年,微软就拥有一个可以与谷歌文档相媲美的产品,但最终却因政治原因被扼杀。NetMeeting和其他一些前景看好的产品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当然,微软并非唯一一家内部政治斗争激烈的公司,但它以政治斗争的残酷程度而闻名。
虽然鲍尔默在整顿内部事务方面做得并不完美,但当我还在微软工作时,我曾询问过一些因内部政治斗争而被搁置或扼杀的有前途的项目,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鲍尔默时期都被清除出去,这使得纳德拉接手时,公司运转得更加高效。
大局
从宏观角度来看,鲍尔默接手的是一家财务状况稳健的公司,但其内部和外部政治斗争令外界普遍认为该公司极有可能走向衰落,甚至出现了像格雷厄姆著名的“微软已死”论断——预计微软的收入将在五到十年内下滑。事后看来,盖茨时期采取的措施限制了微软利用其垄断地位彻底扼杀竞争对手的能力,但并没有出现奇迹般的转折点。相反,微软继续在企业产品领域保持强劲的势头,并持续对未来进行合理的投资,成功地取代了那些内部被视为长期死胡同的收入来源,即便这些收入来源最终能够盈利,例如Windows和盒装(非订阅)软件。
与大多数处于类似境地的公司不同,微软愿意大力补贴一系列管理层认为能够推动公司未来几十年发展的创新项目,例如Windows Phone、Bing、Azure、Xbox和HoloLens。从公司内外对这些创新项目的评论可以看出,当现有成功业务的颓势显而易见时,企业很难利用这些成功业务来补贴新业务。人们抨击这些创新是愚蠢之举,会扼杀公司,并认为公司应该将精力集中在最赚钱的业务上,例如Windows。即使有非常明确的 数据表明打破现状是正确的选择,人们通常也不会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如果失败,就会显得愚蠢。但鲍尔默不顾数十年的嘲讽,仍然愿意做出正确的选择。
公司难以进行此类转型的原因之一是,它们通常无法推出与核心业务截然不同的新产品。当谷歌又一款非收购的消费产品失败时,人们往往习以为常——谷歌当然会失败,他们是一家技术至上的公司,产品能力很差。但微软却多次成功转型。Xbox 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看看三大游戏主机制造商,其中两家是历史悠久的硬件公司,另一家是微软——一家从软件公司转型而来,最终掌握了硬件制造技术的公司。Azure 也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如果你看看三大云服务提供商,其中两家是自创立之初就专注于在线服务的公司,另一家是微软——一家从软件公司转型而来,最终掌握了在线服务技术的公司。其他一些核心业务并非硬件和在线服务的公司也看到了这些机会,并试图转型,但最终都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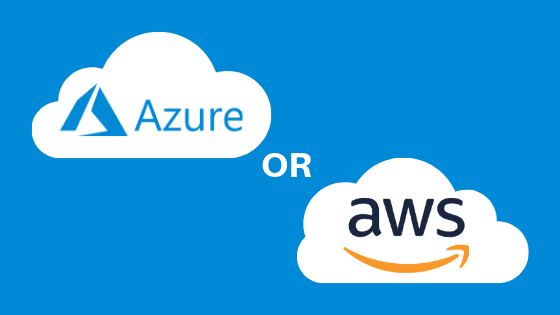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微软的转型过程,就会发现很容易像嘲笑微软的企业销售话术一样嘲笑它。Azure 的核心团队来自 Windows,所以在 Azure 的早期阶段,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事件管理流程。在第一次大规模全球宕机时,人们在走廊里四处询问“Azure 是不是宕机了?”,并试图弄清楚该怎么办。在接下来的几年里,Azure 不断遭遇重大的全球宕机,同时也在摸索如何交付相对可靠的软件。但他们最终还是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打造了一个万亿美元的业务。还有一次,在 Azure 真正掌握服务器构建技术之前,一位微软工程师打开了亚马逊的定价页面,发现 AWS 的磁盘零售价比 Azure 的磁盘配置成本还要低。我在微软的时候,Azure 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跟不上需求。有人开玩笑说,最近大量招聘销售人员的举措效果太好了,导致公司卖出了太多 Azure,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而且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个真正的危机。在其他案例中,微软大多是自行摸索出解决方案,而这次他们从亚马逊引进了一些在供应链和数据中心建设方面拥有深厚专业知识的资深人士。人们很容易说,当你遇到问题而竞争对手又拥有合适的专业知识时,你应该聘请一些专家并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大多数公司在尝试这样做时都会失败。有时,公司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帮助,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引进了资深专家,却无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公司里的元老级人物来说,阻止引进外部资深专家的努力非常容易,尤其是在像微软这样内部纷争不断的公司里,但领导层能够确保此类关键举措取得成功³。
在 Azure 崛起期间,我与谷歌工程师谈论 Azure 时,他们普遍对 Azure 持否定态度,并会嘲笑它存在上述问题。这对于那些在大型在线服务公司工作、拥有运营大规模服务、构建高效硬件和建设数据中心方面深厚专业知识的公司工作的工程师来说,显得十分滑稽。然而,尽管微软在技术、运营和文化方面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但它仍然凭借 Azure 建立了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业务部门。
并非所有投资都取得了成功,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那些批评微软注定失败的评论——他们认为微软投资方向错误,或者说年轻的公司会超越它——那么,如今微软的市值比谷歌高出50%,是Meta的两倍。纵观整个科技行业的历史,微软自1975年成立以来,近五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强劲的执行力,这在科技行业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英特尔的历史稍长一些,但它在世纪之交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并且在过去十年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IBM的历史也很悠久,但它早期的规模并不大。例如,当T.J. Watson将Computing-Tabulating-Recording Company更名为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时,其年收入还远低于1000万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约为1亿美元)。计算机开始变得庞大,IBM在20世纪50年代也成为了科技巨头。然而,1969年针对IBM的反垄断诉讼旷日持久,直到1982年才因“缺乏依据”而被撤销。这场诉讼严重束缚了IBM及其企业文化,其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例如,IBM的各项云计算计划屡屡失败,到了90年代,公司几乎濒临破产,最终依靠格斯特纳的力挽狂澜才得以幸存。如果我们回顾那些曾经长期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老牌公司,会发现它们大多已经不复存在,例如DEC和Data General;或者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几乎走向灭亡,例如IBM和苹果。当然,也有一些公司曾有过类似的长期强劲发展时期,例如Oracle,但它们在拓展业务方面远不及微软高效。因此,Oracle的价值或许只相当于两个必应搜索。这使得甲骨文成为全球市值排名第 20 的上市公司,这当然不算差,但它远不及微软。
如果微软遭遇重大挫折,像英伟达、Meta 或谷歌这样的年轻公司可能会超越微软的成就,但这并非鲍尔默的过错,我们仍然必须承认鲍尔默是一位非常高效的首席执行官,不仅在筹集资金方面,而且在制定愿景方面,都为微软未来五十年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附录:鲍尔默领导下的微软的重要性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重要事件之外,我还能想到一些自格雷厄姆宣布微软“死亡”以来,在鲍尔默领导下发生的有趣的事情。
2007年:微软发布LINQ,即使以如今从业者的标准来看,它仍然相当不错。
2011年:微软研究院的Sumit Gulwani发表了题为“使用输入输出示例实现电子表格中字符串处理的自动化”的论文,该论文在10年后被评为最具影响力的POPL论文之一。
本文探讨了如何使用程序合成技术实现电子表格的“自动完成/推理”。
我并不喜欢专利,但我猜测Excel中自动完成/推断功能运行良好而Google Sheets中几乎完全失效的原因在于,微软基于这项研究拥有专利。
2012年:微软发布TypeScript
这无疑是本世纪发布使用最广泛的编程语言,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使用最广泛的编程语言(只要你不把 TS 的使用也算作 JS 的使用)。
2012年:微软Surface发布
自帕诺斯·帕奈 (Panos Panay) 于 2022 年离职以来,Surface 产品线的前景一直不容乐观。即使在 2022 年,它也算得上是一次失败。然而,Surface 在 2022 年的年收入高达 70 亿美元,这足以说明微软的规模和成功——大多数公司都梦寐以求能拥有像微软这样年收入 70 亿美元却最终失败的业务。
2015 年:微软发布 vscode(虽然是在鲍尔默 2014 年卸任之后,但这项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源于鲍尔默任期内的工作)。
如今,VS Code 似乎是程序员中最广泛使用的编辑器,而且优势非常明显。几年前我查看相关调查数据时,就被它如此迅速的发展速度震惊了。VS Code 似乎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序员编辑器统治地位。或许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是十年前保罗·麦卡特尼宣布微软已死之前的 Visual Studio,但由于它实际上仅限于 Windows 系统,而且价格不菲,因此从未达到过 VS Code 的市场份额。
希思·博德斯指出,2011年受聘的埃里希·伽玛在这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微软取得的巨大财务成功,无论是鲍尔默领导下直接取得的成功,还是鲍尔默之后建立的成功,都引发了一种反响:微软虽然财务成功,但对那些追捧潮流的程序员来说却无关紧要,就像IBM一样。举个例子,如果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Bing搜索量,IBM的价值可能只有0或1个Bing搜索量。但即便我们抛开财务因素,仅仅考察每家市值1万亿美元的科技公司(苹果、英伟达、微软、谷歌、亚马逊和Meta)对程序员的影响,英伟达、苹果和微软都拥有大量依赖于这些公司的程序员,因为他们依赖于这些公司的生态系统(CUDA、iOS、.NET和Windows,其中Windows至今仍是许多大型领域,例如3A游戏的首选平台)。
你可以为大型云供应商辩护,但我认为企业对 AWS 的依赖程度并不像一家严肃的英语消费者应用公司那样强烈,该公司确实需要 iOS 应用,或者一家 AAA 游戏公司必须在 Windows 上发布游戏,并且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在 Windows 上进行开发。
如果我们关注那些不局限于特定生态系统的程序员,微软由于其开发的 VS Code 和 TypeScript 等工具,对很多程序员来说都至关重要。我并不认为它一定比亚马逊更重要,毕竟很多程序员都在使用 AWS,但很难否认,在鲍尔默的领导下,微软(以及其他许多公司)开发出了 VS Code 和 TypeScript 等工具,这对程序员来说意义非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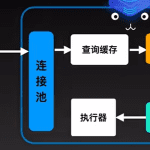



 苏公网安备32021302001419号
苏公网安备32021302001419号